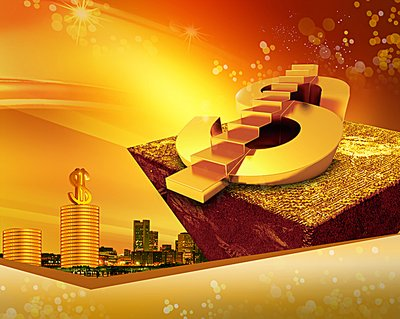徐志摩翻译李清照的词,三分玄妙,七分好笑

刚才向花担买得一枝春花,新鲜得很。泪珠般的朝露,还未干呢!
恐怕那个人会笑我“没有春花长得好看”。我要戴起来,定要他说出我好看还是花好看。
这位女子的心情,真个世代都会有,长久不会变的。真是一首单纯有趣的诗。可我要说,这是一首翻译诗,你一定会觉着翻译得浑成;假若说,原作是一首古代的词作,你或许会感到惊奇。初读到这首诗,我就有这种特别的惊奇感受。

这首诗的题目,是一个词牌《减字花木兰》。它的原作,出自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之笔:
卖花担上,买得一枝春欲放。泪染轻匀,犹带彤霞晓露痕。
怕郎猜道,奴面不如花面好,云鬓斜簪,徒要教郎比并看。
简单看看。原词的色调浓度似乎比译成的诗作要“稠”。“泪染轻匀,犹带彤霞晓露痕”被“泪珠般的朝露,还未干呢”这样轻倩明晓的句子替代;“云鬓斜簪,徒要教郎比并看”更由比原作略显俏皮的“我要戴起来,定要他说出我好看还是花好看”来表达。夸张一点说,翻译不仅不逊于原作,还传递出许多现代鲜活的气息。
这首翻译诗,出自我国现代著名诗人徐志摩之手。大约在1924年(古建专家,徐志摩表妹夫陈从周根据字体推断),正在诗歌创作探索中的徐志摩,读起了一部李清照的《漱玉词》。吟诵之间,来了兴致,便试着用白话,以新诗的笔调,陆续翻译起来。前前后后,译出十多首。
这批译作,当时似乎并无发表的意思,就随手交给了同乡,也是留学归国的学者张歆海。张歆海与徐志摩交谊深厚,徐志摩飞机失事的前一晚,就住在张歆海南京的家里。
这批译稿手迹,张歆海没有轻易随意处理,而是带着它在身边数十年。晚年张歆海在美国定居,徐志摩的儿子徐积锴去看望这位父亲老友时,张歆海拿出了这批十二张复印出的徐志摩译诗交给他。1985年4月,徐积锴从美国回来为父亲扫墓,返回时将这些资料交给了曾经写出过《徐志摩年谱》的陈从周。
对于一位现代新诗创作的重要人物,这批作品体现了诗人学习和创作的深广“幅面”。不久,陈从周将这些白话译作发表在一家“史料”杂志上。该杂志发行量不大,数十年来,它们似乎没有引起读者怎么关注。
笔者在对照原词逐字句体味这些译作后,感到对于古典诗词的阅读,传播,这批作品有颇为独到,可资参照的地方。空说无凭,我们不妨捡择数首来比对一番。
秋天的光景是不错的,不过我有一点伤感。看见菊花黄又晓得是重阳快到了。风也到了,雨也到了,凉也到了,不能不加一件衣吃一杯酒。
醉醒来又是黄昏的时候,孤零得可怕,凄凉得难过。这么长的夜,还有捣衣声,虫叫声,更漏声,震动耳鼓,打动心门,一个人对着明月怎睡得着呢?
这首诗,对应的是李清照有名的《行香子》:
天与秋光,转转情伤。探金英,知近重阳。薄衣初试,绿蚁初尝。渐一番风,一番雨,一番凉。
黄昏院落,凄凄惶惶。酒醒时,往事愁肠。那堪永夜,明月空床。闻砧声捣,蛩声细,漏声长。
徐志摩的诗译,上阕的下节,来得颇为清丽流畅。可对照原词,却是调整了先后。在李清照,加衣,尝酒,先说;风雨添凉,随后。自是一种巧思。可徐志摩的风、雨、凉之后,“不能不加一件衣吃一杯酒”将原词两句融会合一,有一种叠加,紧凑同时又延展的新诗风味,不仅原作词意不失,表达上也考验了汉语的结构弹性。
原词下阕后半节“那堪永夜,明月空床。闻砧声捣,蛩声细,漏声长。”李清照写时在字眼选择上,颇为用心。蛩声“细”,漏声“长”,砧声却将动词“捣”后置来形容,不仅有创意同时表达确切。
面对如此完美的原作,徐志摩在翻译时不得不加附一些解说文字——“震动耳鼓,打动心门”云云,并且将“明月空床”四字内容移作结尾:“一个人对着明月怎睡得着呢?”看来,原作愈精美,翻译愈发不易。
李清照有一首《蝶恋花》,情境语意,都别具风格:
永夜恹恹欢意少。空梦长安,认取长安道。为报今年春色好。花光月影宣相照。
随意杯盘虽草草。酒美梅酸,恰称人怀抱。醉莫插花花莫笑。可怜春似人将老。
且看徐志摩如何应对:
这样的长夜,真不好过。去是想去的,怎么去呢?告诉他快些回来吧,大好的青春,不要辜负啊。
随便吃一杯呢,有点醉意有点酸意也活得有趣。不要笑我这个年纪还要戴花。不只我老了,春也快老呢!
徐志摩的这首诗,翻译时舍去了原作中的一些具象。譬如“长安”,原作里两次出现,翻译中却不见了。大家知道,“长安”此时可代指京都“汴梁”,是指想念之人所去的地方,一般并非实指。
为了避免翻译出来还需注释,徐志摩干脆虚化处理了,只保留真实心情。原作里有杯有盘,有酒有梅子,徐志摩也不让它们出现。后者只用它们的滋味替代,效果也很好。
白话大多较文言松弛,故翻译来一般都长出一些,可徐志摩的节略,有时让白话几乎与文言相若。“空梦长安,认取长安道”九字,徐志摩翻译成“去是想去的,怎么去呢?”也是九字。(当然,这句翻译,必须放在诗中才能显现其意味来)“随意杯盘虽草草”七字,徐志摩干脆用“随便吃一杯呢”六字打理,也是取其神而舍去形。
这首诗译中笔者极喜欢的,是用“有点醉意有点酸意也活得有趣”来翻译“酒美梅酸,恰称人怀抱。”无论舍去具象,演绎内蕴,还是添加字句,完整意象,都是为了使翻译与原作“恰称”,并能成为独立可赏的新诗。通体读去,徐志摩应该有这样的想法才是。

另有一首诗,我们先来读读:
躲起小阁来,日子虽然显长,也觉得深幽有趣。炉香已过,天也晚了,种的梅花很不错呀,何必要到外面看去?寂寞是寂寞一点,从前何先生在扬州时不是这样吗?
要晓得梅花不是讲热闹的,也经不起风雨,现在这样零落,我太难过了。由他去吧,感情是永远不能磨灭的,再到了有月亮的时候,对他的零落影子也一样可爱。
此作品名为《满庭芳·残梅》。我们也来看看宋时的李清照如何表达惨淡梅花:
小阁藏春,闲窗锁昼,画堂无限深幽。篆香烧尽,日影下帘钩。手种江梅更好,又何必,临水登楼。无人到,寂寥浑似,何逊在扬州。
从来知韵胜,难堪雨藉,不耐风揉。更谁家横笛,吹动浓愁。莫恨香消雪减,须信道,扫迹情留。难言处,良宵淡月,疏影尚风流。
词中何逊,是魏晋时期梁代诗人。他有很好的写梅花的诗句,连杜甫也赞叹:“东阁官梅动诗兴,还如何逊在扬州。”这首词的翻译,徐志摩用了许多很白话的句子,来试图稀释原作浓稠的典雅。
譬如,以轻倩家常的“炉香已过,天也晚了”对应“篆香烧尽,日影下帘钩”。避免了“篆香”“帘钩”这些词语的解说;“又何必,临水登楼”这样的套语,徐志摩干脆用一句“何必要到外面看去?”真正化繁为简,得其精神。
“无人到,寂寞浑似,何逊在扬州”这几句,要想跟随,怕不容易。徐志摩却说:“寂寞是寂寞一点,从前何先生在扬州时不是这样吗?”颇清畅。“何先生”翻“何逊”,接通遥远。叫人感觉一千多年前的诗人,成了自己今天生活中熟识的“先生”一般。
下阕的翻译,徐志摩的处理略嫌简单了些。“难堪雨藉,不耐风揉”体味起来,风雨的恣肆都出来了,用“也经不起风雨”对应,那种周折委曲之态,淡了许多。
只“感情是永远不能磨灭的”翻译“须信道,扫迹情留”,显得现代。“再到有月亮的时候”处理“良宵淡月”句,程度、层次都没有关联到;现代滥的“可爱”对“风流”,内涵照应实在不足。
有一首《渔家傲》,翻译得也是不错的:
下雪了,春快来了,梅花也妆扮起来呢,好像半面美人儿刚才出浴的样子。
天公也凑趣呢,你看这样好月亮,花前月下,怎好不吃一杯,何况对着这样好梅花。
李清照的原词:
雪里已知春信至,寒梅点缀琼枝腻。香脸半开娇旖旎。当庭际,玉人浴出新妆洗。
造化可能偏有意,故教明月玲珑地。共赏金尊沉绿蚁。莫辞醉,此花不与群花比。
李清照的运笔大胆出新。将雪里寒梅用“当庭际,玉人浴出新妆洗”描摹。这样的内容,近现代见过许多,徐志摩便追影随形,以“好像半面美人儿刚才出浴的样子”对应;“共赏金尊沉绿蚁”,徐志摩分解成两句:“花前月下,怎好不吃一杯……”“花前月下”似乎俗旧了些,可对“共赏”二字,它就颇为现成相埒。
“怎好不吃一杯”舍了“金尊”“绿蚁”这样的具象代词,使现代人一目了然。这首词对应最佳处,笔者以为在“天公也很凑趣呢”与“造化可能偏有意”之间。字词调换了,意思却全照应到;尤其风味未失,大不易。

李清照的一首《怨王孙》,很受人们喜欢:
帝里春晚,重门深院。草绿阶前,暮天雁断。楼上远信谁传?恨绵绵。
多情自是多沾惹。难拚舍。又是寒食也。秋千巷陌人静,皎月初斜,浸梨花。
因为原作情绪表达完满,徐志摩的翻译,似乎也只是追摹:
困处在深闺,春要快去了,行人一点的消息也没有。寄一个信给他么?托谁寄呢?这怎么好。
多情的自然是什么都放不下。寒食又到了,这静悄,秋千也空着,只有向月亮浸着白白的梨花。
徐志摩大约要让翻译成为真正的新诗,将一些可出彩的如“草绿阶前,暮天雁断”这样古诗词中常常的具象、色调,以及“暮天雁”等,都弃去了。没了大雁,这“信”就真不知“托谁寄呢”?
李清照的“多情”,用了“沾惹”这个意味繁复的词,徐志摩虽然竭力,可“什么也放不下”实在难能将“沾”“惹”这样牵连彼此的微细层次感浮现出来。
李清照,本是一有兴趣才情,有丰富含蕴的女子。不料时代弄人,遭逢国破家亡。她的感触,写出词来,就叫千载后人,为之无限追怀。且看她一首回顾早年,对应当时的《转调满庭芳》:
芳草池塘,绿阴庭院,晚晴寒透窗纱。玉钩金鏁,管是客来唦。寂寞尊前席上,唯愁海角天涯。能留否?酴釄落尽,犹赖有梨花。
当年曾胜赏,生香熏袖,活火分茶。极目犹龙骄马,流水轻车。不怕风狂雨骤,恰才称,煮酒残花。如今也,不成怀抱,得似旧时那?
(此词流传中,略有残损。现据一般本,也与徐志摩翻译比对照录。)
这首词,徐志摩翻译得较为从容:
池边青草,院里绿阴,向窗外一望,晚晴真好啊!帘也打起来,门也打开来,有客来么,正好。我一个人吃酒正觉得寂寞。又想起行人未归,好不难过。坐下吃一杯酒吧,荼蘼是开过了,还有梨花可赏呢。
不要谈到从前赏花的胜会,打扮起来,高朋满座,看着外面的王孙公子,车水马龙。虽然遇到风雨,依然觉得痛快。如今没有这种兴会了,这样的好时节也是空的。
原词中的“荼蘼”(“酴釄”另一写法),是一种蔷薇科的草本植物,花朵不大,较为繁密。这首词的翻译,徐志摩开始部分,对原词追随得很紧,前几句几乎字句变动不大。“玉钩金鏁”(鏁,古同“锁”有人以为,“锁”是闭门,所以可能文字有问题。)徐志摩用“帘也起来,门也打开来……”一译,原文就顺了。“锁”可以闭门,也可来开门的。
“管是客来唦”一句,显示了诗词大家创制的一面。虽然前面也有人语气词入诗入词,可民间多些,文人中却大家多些。李清照此词中用了数处,顺心随性,显出她创造的不拘一格。徐志摩以“有客来么,正好”次序颠倒,也算是对原作妙语的合适回应。
下阕的开始,作品以“当年曾胜赏……”引出旧时的风华溢彩,“犹龙骄马”“流水轻车”云云。可不知为何徐志摩在翻译时,先加附了“不要谈到”几字。词作者显然是要通过充分表现当年的华彩,来与今天的零落比对,故此结尾处有“如今也,不成怀抱,得似旧时那”几句,造成映照强烈的艺术效果。
这种手法,古今人都懂得,可不能预先说破。不知徐志摩当时为何没留意到,把该放在最后的话提到了前面,使得效果程度减弱。这或许是他不意间的失笔吧。

有一首短词《品令》,对着秋天,写出与荷花间的交流:
急雨惊秋晓。今岁较,秋风早。一觞一咏,更须莫负,晚风残照。可惜莲花已谢,莲房尚小。
汀萍岸草,怎称得,人情好。有些言语,也待醉折,荷花问道。道与荷花,人比去年总老。
李清照的“秋”,都写得好。到底是大家,每每有独自创意。这一首,对着莲花,喝酒作诗。可觉着有些话,还是不能不在饮醉时说出:“人比去年总老。”这是无限感慨,也是无限留恋。
徐志摩的译笔,追随得也紧:
啊!秋雨来了,今年来得这样早呢?对着这黄昏雨景,那不能不吃一杯酒,写一首诗。莲花的季节快完了,莲房还小呢。
花草虽然有情,怎比得人情好呢。有一句话,我要待酒后向荷花问一问,“你比去年老了一些么,我呢?”
前边的翻译,是顺遂着原作。结语处“道与荷花,人比去年总老。”李清照显然是希望乘醉对着荷花说说伤心语。徐志摩却用了反问的句式:“你比去年老了一些么,我呢?”虽然是知道答案的反问,可到底口吻不一致。李清照是肯定的,只是借着一个对象——荷花,倾诉。意味无穷。徐志摩的反问句式,对原本的表达程度,似乎减弱了。
徐志摩这批翻译,无法一一拿出介绍。我们用李清照的一首著名词作及翻译来作结吧——《永遇乐》:
落日熔金,暮云合璧,人在何处?染柳烟浓,吹梅笛怨,春意知几许?元宵佳节,融和天气,次第岂无风雨。来相召,香车宝马,谢他酒朋诗侣。
中州盛日,闺门多瑕,记得偏重三五。铺翠冠儿,捻金雪柳,簇带争济楚,如今憔悴,云鬟雪鬓,怕见夜间出去。不如向,帘儿底下,听人笑语。
这首词以繁华写悲凉,极是感人。古人有读此词而“为之涕下”者,可知古今同心。徐志摩的翻译,虽跟随原作较紧,可自在之态依然:
夕阳衬着的暮云特别艳丽,那人去的还未归。还有柳啊,梅啊,春天也不早,元宵快到,现在虽然晴和,到时候的风雨恐怕免不了。诗朋酒友啊,不要劳驾吧!
想起在中州的快活日子,重阳啦,端五啦,说不尽的热闹。如今这个年头,打扮已经懒了,更不说到去逛。只管听着人家顽吧。

原作中的“三五”,应该还是指“元宵节”,为避与上面重复改称如此。可徐志摩却翻译成“重阳啦,端五啦……”不能说确切。可笔者以为,徐志摩有他的道理。李清照当年的“盛日”,当然不限于“元宵”。中国人旧时重要的节日,她都该参与并快乐着。这是原作应有却未说明之意,所以不好认为是徐志摩理解的问题。结尾处的几句,是该词紧要之点。
试想,一个女子眼下“憔悴”到“风鬟霜鬓”,该是怎样的心情?外面的快乐,似乎都“怕见”。“帘儿底下,听人笑语”句,不愿看却想听听,那种“曾经沧海”的复杂心情,通过寻常的文字获得到强烈表达。这样富有张力的文辞,徐志摩实在不易应付。他的翻译,调子清淡了些。那些造成心理冲击力的状态描述,传达得实在不充分。诗词的不易翻译,甚至不能译的观点,在诗人徐志摩这里再度印证了一回。
可我们读了徐志摩这些对李清照词的翻译,还是有许多的感受,领会,甚至悦赏。整体看去,徐志摩虽是在翻译,可他追求的结果,是可读之诗。对原作,他更重视传神,并不为原词过分牵系。这从他常常调整原作文字次序,舍弃一些具象,尤其典故等可以看得很清楚。这种翻译理念,在“五四”前后时期其实颇为盛行。
当然,万事难能两全。仅从徐志摩翻译的这批作品看,优秀者堪称传神,有时的创意令人叹服,单独出来依然是绝佳诗作;但有些由于舍弃较多,不及原作丰厚,在传递其中特有的韵致方面,“稍逊风骚”……既然诗词有不易译,甚至不能译的说法,实际的需要又让人不得不“戴着镣铐跳舞”。
在我们读到许多亦步亦趋,呆板僵硬的古典诗文翻译后,读一读徐志摩当年的诗译探索,也许会有新的启发,多一点接近古人心情的思路。这也许是笔者一一详加比对,介绍这批白话翻译的初衷和动因。
徐志摩是“五四”时期的一代名家,出国留过学,诗歌也写得相当“洋派”,可他并不排斥我国古代文化精华。这批白话翻译,可以视为其向中国古典诗词的致敬。现在有一种说法,认为“五四”那一代文化人,抛弃甚至“割裂”了传统。绝对不确实。
“新文化运动”的引领者胡适,以多篇中国古典小说考证及佛经,《水经注》等古文化研究,开一代风习(眼下有些人甚至称其为“国学大师”);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《汉文学史纲要》,是一流上等的研究佳构;陈独秀有《老子考略》《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》等著述,他的最后著作《小学识字教本》,人称文字学研究集大成者……
他们所排斥反对的,是旧有文化中束缚人性的那些糟粕,这在他们的著述中分得十分清楚。今天我们介绍的这批徐志摩翻译,堪称又一确切证据。这也许是不算脱题的应有之意罢。